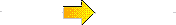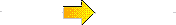此刻,栋居的眼前正浮现着一幅情景,一幅令他感到厌恶而不愿回想起的情景。但是,
那幅情景却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始终不肯离去,只要他还活着,恐怕是无法甩掉了。
也可以说,他是为了终生追踪在这一情景中出现的人物,才当了刑警的。对于心中出现
的那种景象,他虽然不愿想起,但却也不能忘怀,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它,他才能活到了
今天。
栋居很不相信人类,取而代之的是憎恨。人这种动物,无论是谁,如果追究到底,都可
以还原为“丑恶”这个元素。无论戴着多么高尚的道德家、德高望重的圣人的面具,夸夸其
谈什么友情和自我牺牲,在其心中的某个角落里都隐藏着明哲保身的如意算盘。
使栋居陷入对人类如此不信任的东西,正是深深地印在他脑海里的那些情景。
他也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而生活着,因此不能显露出这种不信任和憎恶。但是,潜藏在他
内心深处的对人类的不信任和憎恶,已经成为不可化解的瘤疾,就像与某些人终生相伴的肿
瘤一样,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却会顽固地一直存在下去。
甚至可以说。它是栋居精神的细胞物质、把它封闭起来不加暴露,是为了能够活下去的
一种权宜之计。
栋居没有见过母亲的容貌。母亲并不是因病去世才离开他的。而是在他还不懂事的时
候,找了个男人,抛弃了年幼的栋居和自己的丈夫,跟着那个男人跑了。
从那以后,栋居便由父亲一手拉扯长大。父亲对于妻子跟着别的男人跑掉这件事,从来
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出身于教师家庭的父亲,自己也是个小学教员,在战后那混乱的局
面下,他为了孩子们的教育事业而奉献了自己。
这样一位父亲,对于那位事事都喜欢出风头的母亲来说,也许会令她感到窒息吧?父亲
由于高度近视而幸免被拉去当兵。但在当时军国主义盛行的社会里,那种情况对于母亲来
说,好象也成了一件令她觉得十分难堪的事情。
后来听别人说,她在“枪后会”的集会上结识了一些年轻军官,并经常同他们一起四处
游荡。据说母亲逃离父亲身边也是因为她与那些军官当中的一人打得十分火热,结果跟着那
人去了他上任的地方。
父亲虽然没有对栋居吐露过什么抱怨的话,但他却在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忍受着妻子与
别人私奔后所留下的寂寞。栋居是他的精神寄托,他全靠栋居来安慰他那颗孤独的心,那是
个只有一位父亲和一个儿子的寂寞家庭。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社会上的情况混乱不堪,母亲跟着那个军人走了之后,情况究竟如
何,他们不得而知。但是,社会上的混乱对于他们父子二人的家庭却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
响。不知道是由于父亲的呵护,还是因为自己的遗忘,栋居对于那一段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
了。也许是由于没有母亲的寂寞感覆盖了他幼小的心灵,使他没有注意到社会的变迁。
只有寂寞清晰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之中,与父亲围在一起吃晚饭的寂寞、灯光的昏暗、房
间的寒冷,至今仍刻骨铭心地留下了记忆。没有母亲的寂寞掩盖了食物的短缺,那寂寞感已
经变成了他对母亲的怨恨,是她抛弃了父亲和自己。
这个不知道母亲长相的孩子知道了母亲还活在天底下的某个地方,便对她的模样产生了
一种油然而生的怀念和憎恶。
但是,父亲还活着的时候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他和父亲一起分担着寂寞,父子二人相
依为命,避开了人世间严酷的风刀霜剑。那是他们父子二人与世隔绝的一片小天地。
可是没过多久,栋居却失去了这位唯一的保护者。
事情发生在栋居4岁那年的冬天。那一天,栋居在车站前面等待着父亲的归来。在傍晚
的固定时间去迎接下班回来的父亲,这是栋居每天必做的事情。
父亲每天用芋头和玉米为栋居做好盒饭之后才离开家。从那个时候起直到傍晚,栋居就
一个人守在家中。当时既没有电视,也没有连环画册,他待在昏暗的屋子里,一心一意地盼
望着父亲回家时刻的到来。
虽然父亲说外边有危险,不让他出来迎接,但傍晚去车站迎接父亲,对于年幼的栋居来
说,是唯一的乐趣了。一看到父亲的身影从检票口出来,栋居就马上像只小狗似地扑过去,
吊在他的手上。父亲每次都必定会给他带点小礼物回来,虽然父亲嘴上说不许来接,但栋居
来接,父亲还是很高兴的。
礼物都是用芋头做的包干或者是用大豆做的面包。但是,那些东西对于栋居来说,已经
是最好的食品了,那些礼物上面带着父亲那双大手的温暖。
从车站回家,一路上的谈话是父子之间最幸福的时刻。父亲眯缝着眼睛,听栋居口齿不
清他讲述着自己一个人在家时的各种各样的冒险故事。
像什么把迷了路窜进家里来的野猫赶出去的故事,什么来了个乞丐往家中窥视时的恐怖
经历,还有到隔壁的小吉家去时人家拿出来的点心多么香甜等等,这些不着边际的故事层出
不穷,父亲“是么是么”地搭着腔,十分怜爱地听着他讲。
父亲如果没有按时回来,栋居就会一直等下去,直到他回来为止。年幼的孩子被寒风吹
得缩起身子等在那里,也没有什么人去理会他,当时流浪的大人和孩子到处都是,一个年幼
的孩子独自游来逛去也并没有什么稀奇。
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寻找自己的活路,谁也没心思去管别人的闲事。
那天,父亲比平时晚回来了大约30分钟左右。那是2月底最寒冷的季节,在检票口看
到父亲身影的时候,栋居那小小的身体已经快要冻僵了。
“你怎么又来了?说了多少遍叫你不要来的嘛!”
父亲紧紧地抱住了栋居那已经冻僵的整个身体。父亲的身体也冻僵了。但是他心中的那
片温暖却仿佛传到了栋居的身上。
“今天哪,我给你带回来了特别棒的礼物哟!”
父亲故弄玄虚地说。
“是什么呀。爸爸?”
“打开这个看看吧。”
父亲把一个纸袋子递到了栋居的手中,那上面还残留着一丝微温。栋居朝纸袋内张望了
一眼,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惊叹:哎呀!太棒了!
“怎么样,棒吧?那包干里面可是包着真正的馅儿哪!”
“真的?”栋居瞪圆了眼睛。
“当然是真的。是我在黑市上买来的。为了买它,我才回来得晚了些,好啦,赶快回家
去一起吃掉它吧。”
父亲牵住儿子冰凉的小手,给他暖着。
“爸爸,谢谢你!”
“这是给你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的奖励。从明天起。不许你再来接我了,说不定会碰上
可恶的人贩子呢!”
父亲慈详地告诫着栋居。当他们两个人正要回家的时候,那件事发生了。
车站前广场的一角骚动起来月下一带排满了卖来路不明食品的摊贩。吵闹的声音就是从
那一带传过来的。人们正纷纷朝着那边围过去,一个年轻的女人正惊叫着,不断地发出“救
命啊!救命啊!”的求救声。
父亲拉着栋居的手,快步朝那边走去。他们透过人墙的缝隙往里一瞧,只见几个喝得酩
酊大醉的美国兵正在纠缠着一个年轻的女人,那见个年轻的美国兵满口说着下流话,虽然不
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但那副嘴脸却是全世界都通用的。他们正在众目睽睽之下玩弄着
那个年轻的姑娘!
一眼看上去,这些美国兵个个都很强壮。与战败国日本那些骨瘦如柴、弱不禁风的国民
相比。他们有着营养充足的身体和油光发亮的红皮肤,他们体内所积蓄的淫秽能量眼看就要
把他们的身体和皮肤都胀破了。
那可怜的姑娘就像是被一群猫包围起来的一只老鼠,眼看就要被捉弄死了。她已经被剥
掉了衣服,呈现出一副令人惨不忍睹的模样。她就保持着这么一副样子,即将在大庭广众之
下受到奸污,不,她等于已经在受到奸污。
围观的人群与其说是怀着教授之心,倒不如说是出乎意料地碰上了有趣的热闹场面,而
更多的怀着一种等着看热闹的残酷的好奇心。就算是他们有心搭救她,也因为对方是占领军
的士兵而无能为力。
对方作为战胜国的军队,一切都凌驾于日本之上。他们瓦解了日本军队:否定了日本至
高无上的权威一一一天皇的神圣地位。也就是说,他们高高地坐在日本人奉若神明的天皇之
上,统治着日本。他们使天皇成为附庸。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已经成了新的神明。
对于占领军这支“神圣的军队”,警察也无法插手干预。对于占领军来说,日本人根本
就算不上是人。他们把日本人看得比动物还要低贱,所以他们才能做出这种旁若无人的放荡
行为。
成了美国兵牺牲品的姑娘,已经陷入了绝望的状态。围观的人们,谁也不插手,也没有
人去叫警察。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去叫.警察也无能力力。
被他们抓住的那个女人算是倒太霉了。
这时,父亲用双手拨开了人群,挤到前面去,对那些眼看着就要对那个女人进行蹂躏的
士兵们用英语说了些什么。父亲多少懂得一点英语。
美国兵们好象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会有这么有勇气的日本人。他们惊讶地一下子把
视线全都集中到了父亲的身上,围在周围的人群也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等待着事态的进一
步发展。刹那间,那里出现了一片令人感到毛骨惊然的寂静。
稍挫了锐气的美国兵们,看清了对手原来是一个非常瘦弱、戴着眼镜的贫寒的日本人。
马上就恢复了嚣张的气焰。
“You,yellowmonkey!(你这个黄种猴!)”
“DirtyJapan!(肮脏的日本人!)”
“Asonofabitch!(混蛋!)”
他们一边七嘴八舌地骂着,一边朝父亲逼过来,父亲拼命地向对方做着徒劳无益的解
释。
但是,美国兵似乎被新出现的猎物激发起了虐待狂的兴奋,他们走过来围成了一圈,开
始对父亲进行推残,就像是凶残的野兽要把营养不良的猎物玩来玩去地捉弄死一样。美国兵
们陶醉于残酷的喜悦之中,惨无人道地折磨着完全没有抵抗和反击的对手。
“住手,不许打我父亲!”
栋居想要救自己的父亲,就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一个美国兵,那是个长得像一头红色魔
鬼似的白人,他的胳膊上有一块好象是烧伤的伤疤。也许是在战场上负的伤。那发红的裂口
处长着金色的汗毛,他那粗壮的胳膊一抡,栋居就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了,父亲带回来的包干
从栋居的怀中掉了出来,滚到了地上。美国兵那结实的军用皮靴轻而易举地就将它踩得稀巴
烂。
在包干滚落的地方,父亲就像一捆破布似地遭到美国兵的痛打,他们拳打脚踢,口吐唾
沫,父亲的眼镜被打飞了,镜片也碎成了粉未。“围攻”的场面深深地印在栋居的记忆中。
“谁来救救我爸爸吧!”
年幼的栋居向周围的人群求救。但是,被他所哀求的大人们。要么耸耸肩膀。把脸扭向
一旁:要么就只是冷冷地一笑。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教援之手。
父亲要搭救的那个年轻姑娘已经连个影子也看不见了,看来她是把父亲作为替身而溜之
大吉了,父亲是为了救她才挺身而出的,没想到却成了她的替罪羊!
如果仅凭解释不清的正义感而伸出手来,那么下一次自己就会被当成第二只替罪羊。正
因为人们亲眼目睹了父亲被当成替罪羊的活生生的事例,所以他们才越发感到害怕。
“求求你们,救救我爸爸吧!”
栋居一边哭泣,一边哀求着。但是每个人都在装聋作哑。既不想从这个地方溜掉,也不
想伸出援救之手,仅仅像是隔岸观火似的表现出一副好奇心,静观着事态的发展。
突然。美国兵哈哈大笑起来。栋居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美国兵正朝着已经精疲力尽、
一动也不动的父亲身上撒尿。他正是那个胳膊上有着烧伤似的红色疤痕的士兵!其他的美国
兵也都模仿着他的样子去干。在“倾盆的尿雨”之中,父亲好象已经意识不到浇在自己身上
的是什么东西了,看到这种情形,不仅是美国兵,连瞧热闹的人也都笑了起来。
比起朝父亲撒尿的美国兵来,栋居更加憎恶在一旁看热闹的日本人。栋居泪流满面,但
他觉得那并不是泪水,而是从心中被剜了一刀的伤口溅出来的鲜血,从眼睛里冒了出来,他
在幼小的心灵中暗自下定了决心:决不能忘记这个场面!
为了有朝一日报仇雪恨,他要把这个场面牢牢地铭刻在记忆之中。敌人就是在场的所有
人!美国兵、兴致勃勃地看热闹的人、被父亲所搭救却把父亲当作替身而逃之夭夭的年轻女
人,他们所有人都是自己的敌人!
美国兵终于打够了父亲,转身扬长而去。围观的人群也散开了。直到这时,警察才终于
见面。
“对方是占领军,我也无能为力呀!”
警察有气无力他说着,仅仅是走形式地做了做调查记录。他那种口气好象是在说,人没
有被打死就算是很幸运了。那个时候,栋居把那个警察也算进了敌人的行列之中。
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右边的锁骨和肋骨也断了两根。医生诊断,父亲的伤势需要用两
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全治愈。但是,由于那个时候的检查粗枝大叶,医生没有发现父亲颅内出
血。
3天之后,父亲陷入昏迷状态,那天深夜,父亲在胡话中。叫着栋居和妻子的名字,咽
下了最后一口气。
从那个时候起,将父亲和自己都抛弃的母亲,还有那个马马虎虎置父亲于死地的医生,
都成了栋居终生的仇敌。
他对人类的不信任和憎恶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培养起来的。他并不记得每一个仇敌的容
貌和姓名,甚至连母亲的长相都不知道,所以,他的仇敌是当时在场的美国兵、围观的人
群、年轻的女人、警察、还有医生和母亲所代表的所有人。
只要对手是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行,栋居打算要一个一个慢慢地对他们进行报复。成
了孤儿的栋居在当上刑警之前,其经历是非常坎坷曲折的,但是,他成为刑警的动机比那坎
坷曲折的经历更为重要。
刑警可以肩负着国家的权力(哪怕仅仅是一种形式也罢)去追捕罪犯。对于栋居来说,
不管是罪犯还是仇敌,其实都是一回事,人能够在法律这个正当的名义之下,将人追得走投
无路的职业就是警察。
栋居并不是为了伸张社会正义,而是想置人于无处可逃的死地。然后慢慢地仔细观察他
那绝望和痛苦挣扎的情形。栋居要把那天眼睁睁地看着他父亲被折磨而死的人一个个都找出
来。穷迫不舍,把他们推下无法逃脱的绝望深渊。
如果以犯罪的方式去做这件事的话,就肯定持久不了,反而迟早会有那么一天,自己将
受到追究。但是如果把这件事变成一种正当职业去做的话,就可以一直追捕那些人,直到自
己不干为止。
栋屠并不是为了伸张社会正义,而是为了向整个人类进行报复才当了刑警的。因为要进
行报复,所以重要的是要让那些追捕的对象尽可能地感到痛苦!
由于被害人没有家属,所以约翰尼·霍华德的尸体由美国大使馆代为认领了,决定由日
本方面负责将尸体火化,并且将骨灰暂时埋葬在横滨的外国人墓地中的一个无人祭祀的坟地
角落里,直到有亲属出现为止。
侦破工作完全没有取得进展。虽然根据栋居刑警的发现,已经弄明白了皇家饭店空中餐
厅的夜景与草帽有些相似。但是仅凭这一点,并不能给破案带来任何进展。
对于被害人来说,草帽似乎具有某种重大的意义,但是那意义究竟是什么,却无从了
解。
“据那对恋人说,他们看到有个女人在作案时间前后从公园里出来,那个女人会不会与
本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但是通过随后进行的侦查。在被害人的周围并未发现有这样的
女人存在。
“如果不是这个女人这条线索的话,那么杀人动机会不会是从被害人的国家带到日本来
的呢?”这种意见渐渐地占了上凤。迄今为止,顺着那个女人的线索,主要以日本人为对象
进行了侦查。但是,如果罪犯是来自美国的话。那么就必须改变侦查的方向。
毫无疑问,由于被害人是个外国人,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凶手是外国人“的看法占
了上风,搜查工作也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外国人的犯罪是比较容易暴露的,因为来日本的外
国人人数毕竟有限,而且在出入境之际也不能不留下一些踪迹。
由于在搜查初期阶段没有发现外国嫌疑人,加之由于那对恋人所提供的证词,嫌疑落到
了一个日本女人的身上。所以,搜查方向就倾斜到日本人这边了,但是无论如何追查,也没
有发现更多的踪迹。
于是,警方再一次研究了那对恋人所提供的证词。他们只是在光线不足的黑暗之中,匆
匆瞥了一眼,无论是那个女人的年龄还是她的特征都一概没看清楚。说那个女人像是日本
人。只不过是一种从姿态上判断出来的含糊印象而已。
“虽然那对恋人觉得那个女人像是日本人,但她也很有可能是个外国女人。”
“能否考虑她是个混血儿呢?如果是个混血儿的话,那么姿态看上去大概会很像是个日
本人吧!
“有必要去被害人的国家进行一下调查。
虽然“罪犯是外国人”的看法又逐渐重新得势,但是在日本国内,已经没有剩下什么值
得进行搜查的对象了。被害人投宿的饭店也已经搜查完毕了。
剩下的搜查对象是被害人的国家。但是,又不能派遣搜查人员到美国去,在日本发生的
犯罪案件,其搜查范围仅限于日本国内,与海外有关联的案件,一般都是通过国际刑警组
织,委托对象国协助进行调查。
即使日本方面派搜查人员出国,他们也没有搜查权。所以。在语言不通,地理和风俗习
惯等一切情况都不熟悉的异国土地上、根本无望进行令人满意的搜查工作。除了委托国际刑
警组织,要求帮助调查一下被害人的居住地之外,日本警方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但那里毕
竟是被害人一直生活的地方,或许会留下一些什么痕迹,表明他与罪犯之间的联系吧?
这样进行搜查工作可真让人心急如焚,搜查人员都感到涉外办案所受到的局限。
栋居刑警后来又数次去了东京商务饭店。
“那个地方已经什么都没有啦!”
与他搭档的山路刑警说道。但是,栋居却仍很执着:
“我总觉得那家饭店与本案有牵连。”
“有什么牵连呢?”
“据说霍华德没有预订房间。是突然到了那家饭店的。”
“那位前台经理是那么说的。”
“被害人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得知那家饭店所在位置的呢?”
“那也许是机场向他介绍的,也可能是出租汽车带他去的嘛!”
“在机场介绍的,一般都是些比较有名气的饭店哪!那家饭店才刚刚开业不久,而且又
没有加入饭店协会,如果是出租汽车带他去的话,那家饭店的地点可就有些莫名其妙了。从
机场来的话,一路上下是有许多像什么‘品川’啦、‘新桥’之类的市中心饭店吗?”
“那可不一定。因为凡是出租汽车,对司机来说,只要计价器的数字上升就行了,而且
新宿是第二市中心,实际上也有大饭店嘛!”
“嗯,你说的倒也不错。不过,据说那家饭店是不大住外国人的,听说那里的住宿者当
中,出差的公司职员占多数,而且多是定期来东京的固定客人。被害人既是一个外国人。又
是第一次来日本,却到那里去住宿,我总觉得他好象预先比较熟悉当地的地理情况。”
“熟悉当地的地理情况?但他可是第一次住进那家饭店的呀!”
“是的,因为他这是第一次到日本来嘛。”
“我觉得你太过虑了。也许他从机场搭的那辆车的司机。知道那家饭店。就把他带到那
里去了。”
“哪有这种道理?如果是出租汽车带他去的话,因为他是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所以一
般来说,是不是应该先由司机到前台服务处去问一下有没有房间呢?可是,霍华德却是自己
直接去前台的。”
“不是听说他会说几句日本话吗?”
“即便如此,他也毕竟是第一次来到异国他乡,所以还是委托司机去办要好一些。”
“会是那样一种情况吗?”
山路似乎百思不得其解,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陪着栋居去了商务饭店。这大概是因为他
对栋居的主张多少还是有些同感的吧?
但是,尽管栋居不肯死心,他们从东京商务饭店还是没有取得任何收获。
约翰尼·霍华德仅有的那点儿遗物,都移交给了美国大使馆。他在日本很少的一点点痕
迹也已经完全消失了。
“大概我们对这家饭店估计错了。”
山路带着安慰的神情对栋居说。但是栋居感到很沮丧,根本就无心答话。难道真是像山
路当初所说的那样,被害人只是无意中来到这里的?通过迄今为止进行的搜查,并没有发现
被害人与东京商务饭店之间有任何事前的联系。
就连栋居也开始死心了,他一边心想这次就算是最后一回吧.一边走出饭店大门的时
候,一辆高级轿车停了下来。司机打开了车门,从车上走下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她穿着一
身十分合体的白色大岛绸和服。
“嗯?!”
栋居和她擦肩而过之后,又回过头去望了她一眼。
“有什么不对吗?”
山路问道。
“不。我觉得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刚才过去的那个女人。”
“没错儿,那不是八杉恭子吗?
“她就是八杉恭子?!”
栋居停下了脚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个女人走去的方向。八杉恭子作为家庭问题评论
家,是电视和杂志互相争夺的大红人,她通过与自己的两个孩子进行“母子通信”的书信形
式,出了一本类似“育儿日记”的书。她在书中写了母亲对于临近青春期微妙年龄的孩子应
该如何进行教育的方法,使那本书成了超级畅销书。八杉恭于也因此而一跃成为了大众传媒
的宠儿,那本书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还被译成了英文,介绍到了国外。
她那似乎很有教养的绰约风姿和略带些阴郁的花容月貌,很适合于上电视。她现在看上
去似乎已经是一个“红极一时的电视演员”了。
如果是八杉恭子的话,那栋居在电视或者杂志上认识了她那张脸也并没有什么奇怪,而
记忆却使栋屠在此之前就对那张面孔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勾起栋居回过头去看那张脸的
原因。又并非出于似曾相识。
这是因为,在与她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八杉恭子那张脸的侧面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轻
轻地招唤着他那遥远的记忆。但是,那刺激的强烈程度还不足以打开他记忆的阀门,就像是
水面上荡起的一阵小小涟漪,很快便恢复了原来的平静。目前颇受人们欢迎的恭子那张可以
称得上是“广告脸”的面孔。已经把它吸收得干干净净了。
八杉恭子现在的形象过于强烈,压抑着栋居过去已经淡漠了的记忆。但是,那种记忆是
确实存在的,她并不是作为一个出没于新闻媒介的广为人知的八杉恭子,而是作为一个与自
己有着某种个人联系的八杉恭子。被埋在了一层又一层的已经忘却了的厚壳底下,要想把它
发掘出来,就需要有更加强烈的刺激才行。
虽然栋居确确实实地意识到了那种记忆的存在,但却怎么电回忆不起来,真使他感到心
急火燎却又无可奈何。
“喂,你怎么了?见到真人就看呆啦!”
山路叫了一声一直站在那里陷入了沉思的栋居,栋居突然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可是,八杉恭子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呢?”
栋居用一种像是半带着自言自语的口气说。
“为什么?栋居君,你还不知道吗?”
山路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栋居。
“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呀?”
“八杉恭子是郡阳平的老婆嘛!”
“她是郡阳平的……”
照这么说的话,在饭店的大门口确实是挂着一块写有那个名字的招牌。
“八杉恭子是……那姓郡的……?”
“你当真不知道吗?都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啦!”
“我知道她有孩子,但不知道孩子是她和那姓郡的生的。”
“刑警不多学点儿社会常识是不行的呀!
山路嘲讽似地笑了。虽然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不是属于社会常识方面的知识,但是既然山
路已经知道了,那么它大概就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吧?
郡阳平是当时的执政党——民友党的少壮派头子。他被看作是保守政界“新感觉派”的
旗手,作为党内的评论家也很声名显赫。关于他,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如:“八面玲
珑,但总是见风使舵”;“变化多端的谋略家”;“不像青年人,是个有着出色办事能力和
决断能力的首领”等等。
他被认为是处于政治风暴中心的“台风眼”。对于日前的麻生文彦政权,他虽然采取了
“配合主流派”的立场,可是一旦风云变幻,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会采取自己的行
动,他虽然在表面上打着“刷新党风,解散派系”的旗号,但实际上却以其天生的对人和蔼
可亲和颇有几分故弄玄虚的出色行动,在其它非主流派和中间派当中踏踏实实地争取着支持
者。
很多人都把他看作是一匹黑马,认为他虽然在表面上并没有露出要当下届执政者侯选人
的野心,但作为党内颇有实力的派系。他正稳扎稳打地巩固着自己的阵营,根据“麻生引退
之后”党内形势的动向,他将会与麻生政权的大人物们一起争夺下届政府的领导权。
郡阳平出身于山形县的一户农民家庭,他发奋苦读,大学毕业之后开了家铁工厂。据说
与军方打交道是他时来运转的开始,但是那方面的消息不太准确。他在34岁的时候,出马
参加众议院选举,并第一次当选为众议员。当时他是位无党派人士。
现在他已经55岁,担任着国土政策调查会会长,正满腔热忱地投身于制订国土综合开
发计划,而这份计划将立足于长远的目标。为此,他与金融界的关系最近突然密切起来了。
在家庭中,郡阳平和妻子八杉恭子有一个19岁的儿子和一个17岁的女儿.都是大学
生。据说因为恭子出了超级畅销书。所以郡阳平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了。但是,大概这方面
正是他被称为谋略家的缘故吧?在公开的场合,他尽量地不表露出八杉恭子是自己的妻子,
在电视和杂志的凸版摄影上他也一直是让她以“八杉恭子”的身份活动,而不止她用“郡阳
平夫人”的身份社交。
栋居从山路那里了解到了关于郡阳平的大概情况。八杉恭子到设有郡阳平后援会办事处
的饭店,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即使与她作为一个家庭问题评论家的活动分开,她作为一
个妻子,来到丈夫的办事处,按说也没有任何不妥之处。
“无论如何,八杉恭子也是个大美人哪!”
山路叹了一口气。
“她究竟有多大岁数了?”
“听说有40岁了,但是看上去也就是30岁左右。”
“那么显得年轻吗?”
“想不到吧?我那口子与她也相差不了几岁,但却好象快到‘退休的年龄’啦!郡阳平
可真是个非常幸运的家伙啊!”
“他们是结发夫妻吗?”
“结发夫妻?”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再婚什么的吧?”
“这个问题我可就不大清楚了,既然他们已经有了上大学的儿子和女儿,大概是在很早
以前就结婚了吧?”
“才40岁就有了上大学的孩子,她可真是太早婚啦!”
“也许岁数上多多少少打了些马虎眼儿,但在很早以前就结了婚,这可是确确实实
的。”
“孩子会不会是他们哪一位与前夫或前妻生的呢?”
“那倒没听说过,不过,你小子对这事儿也大关心了吧?”
“因为有些事情我放心不下。”
“对于八杉恭子,哪个男人都会挂在心上的。”
山路好象误会了栋居的意思。
约翰尼·霍华德被害案的搜查工作毫无进展,从国际刑警组织那里也没有传来任何消
息。作为美国警方。虽然接受了调查被害人居住地的要求,但是案件发生在太平洋彼岸的日
本,他们大概并不太清楚应该调查些什么吧?
护照上所标明的被害人现住址是纽约恶名远扬的哈莱姆黑人区。那儿的情况也许就像日
本的山谷或釜崎的棚户区。流浪者们搭有临时住处一样,因为是临时住处,所以也不会留下
什么可能成为线索的东西,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亲属了。
但是,如果那里是他的临时住处,那么在某个地方就应该有他的原住处。可是,美国方
面做出的最初答复里面,却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
对于“合众国”美国来说。一个黑人在异国被杀之类的事情。可能是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的吧?纽约是个凶杀案根本算不上什么新闻的地方。但是,美国警方对于自己国家的公民被
杀。采取如此冷漠的态度。这个能不给日本的搜查本部造成不利的影响。
可是,罪犯也许是个日本人,所以,不管被害人的国家态度如何冷漠,日本警方对于搜
查工作也不能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搜查本部努力地寻找着9月13日被害人入境那天,把他
从羽田机场送到东京商务饭店的那辆出租汽车。
在东京,目前街上跑着汽车公司的出租车2万辆和个体经营的出租汽车二万6千辆。而
且,并不能肯定约翰尼·霍华德从羽田机场就乘坐了出租汽车,但是,目前留给搜查本部的
就只有这么一点少得可怜的线索。
被害人为什么去了东京商务饭店呢?
也许让被害人搭了车的出租汽车司机知道这个情况。
**********************************
感谢一凡 提供
黄金书屋 校对并首家推出
**********************************
转载时请保留以上信息,谢谢!